*本文爲「三聯美食」原創內容

『家鄉的漿水味道,從多年的沉睡中蘇醒過來,只是一想,嘴裏已經泛濫起洶湧的口水了,即使出走半生,歸來依然是個西北人。 』
作者 / louka shao
說來也是慚愧,一直到30出頭的年紀,才做出了人生中第一鍋成功的漿水和酸菜。
對於少年離家漂泊的我來說,那些和漿水酸菜有關的記憶,早已變得模糊不清。直到懷孕之後,因爲前期孕反的厲害,嘴裏總是沒味道。這時候家鄉的漿水味道,仿佛從多年的沉睡中蘇醒過來,只是一想,嘴裏已經泛濫起洶湧的口水了,即使出走半生,歸來依然是個西北人。
反正孕期有着大把的時間,正好復刻一下幼年時在竈台邊看母親投漿水酸菜的場景。昏暗的廚房,通紅的竈台,一堆亂糟糟的柴禾和兩口大缸——一口用來盛清水,一口用來放酸菜,基本上就是記憶中廚房的模樣了。在這片被稱爲"苦甲天下之地",廚房能有這樣的配置,已經算是殷實之家了。
 電視節目《味道》
電視節目《味道》
從記事开始,就見母親整天圍着這兩口缸轉悠,不是忙着打新水添進去,就是忙着"投"一缸新的漿水酸菜出來,否則家裏的男人們就會吹胡子瞪眼,捧着碗抱怨:"沒酸菜還叫人咋喫這個飯"?這時候母親就會打發我們這些小孩子去山上挖些野菜來,最好就是苦苦菜,有的時候也會用些喫剩的芹菜葉子、白菜葉子、蘿卜幹,幾樣混在一起,擇洗幹淨了,放在竈台的籮筐裏,等着我來把水燒开。
也就是在竈台前燒火的時候,我跟母親說"我就不是個燒火的人",也表達了對天天喫漿水酸菜的抗議,結果母親一句話把我堵了回去:"在我手上你就是喫漿水面的命,以後你本事大了再說!"沒辦法,只好低頭服軟,專心燒火,實在無聊了就看母親是怎么投酸菜的。
其實在我們方言裏,有個比“投”更形象的詞叫“餷”,意思是一邊煮一邊攪拌:先是等水开之後,把葉菜蘿卜條焯一遍水,放到缸裏備用;然後另起一鍋水,再把白面玉米面糊攪散之後均勻地倒進鍋裏,晾到溫溫的程度,就可以讓它和葉菜匯合,這時候就得用長長的擀面杖耐心地攪動,直到熱面湯被均勻地攪散,最後少不了一碗漿水引子,有了它才能臥出一缸好漿水。
即使是同一個村子裏面,每一家臥出的漿水,味道也是不盡相同的。有的人家的漿水清亮酸甜,前中後調一應俱全,拿來直接喝很是解渴;炒一炒去做"醋飯"——比如漿水面,味道極爲酸爽;而有的人家做出漿水酸中帶苦,還隱隱有股臭味,只有少部分人喜歡。久而久之,相熟的女人們在漿水的口味上,逐漸开始拉幫結派,投酸菜的時候,去哪家借引子不去哪家,都是有些微妙講究,只是其中的奧妙不是我這等離家多年的人所能參透。
說到漿水和酸菜,有時候我會把兩者混着用,讓人聽着有些迷糊。實際上,它倆的確是混在一起的:酸菜就是那口大缸裏的苦菜、包菜、芹菜、蘿卜、蓮花白等蔬菜原料,漿水就是因發酵而變酸的酸湯,陝西的酸湯面,拿到我們甘肅就是漿水面。跟四川、東北的酸菜比,西北的漿水酸菜更適合調湯做面,尤其是在以前物質匱乏的時候,漿水酸菜,幾乎成爲西北飲食的基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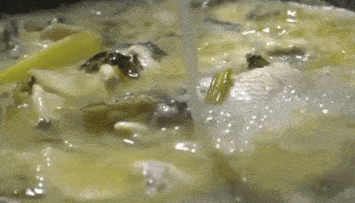 電視節目《致富經》
電視節目《致富經》
最簡單一頓酸飯是這么煉成的:鍋裏燒油,熗爆些蔥花蒜米,然後把漿水酸菜倒進去,頓時一股子酸香就飄出來了,等湯开了之後,不管是洋芋條兒、秋糧面、擀面條還是削面片、面疙瘩,都可以往湯裏下,稀裏糊塗就是一頓飯。聽老人們說,往前年景再不好的時候,全年裏都是漿水酸菜混着各種雜糧煮着喫,甚至只靠酸菜來糊弄肚子,嘴裏總是一股苦酸的發酵味。
當然在我長大的時候,這些靠着漿水酸菜活命的記憶,都已經是上一代人的老黃歷。酸飯——我們把一切喫的都叫作飯——大概率就是漿水面,已經逐漸失去了往日的隆重,客人來家裏做客的時候,主婦都不會做這道上不得台面的喫食,除非是親近到不用拘泥禮數的客人,才會盛上一碗漿水飯,熱熱鬧鬧地圍在一起喫。
作爲基調,漿水酸菜曾經西北飲食的主旋律。漿水可以送到割麥的田間地頭,供勞作了一天的漢子們咕咚咕咚一飲而盡,出一身汗,解一身乏;也作爲每一餐飯的基調,涼菜、炒菜、面食、湯飯.....比如家鄉最簡單的漿水面片,就是將切好的面皮倒入鍋中煮熟,直接在缸中舀出一瓢漿水夾裹着酸菜一同倒入鍋中,攪勻燒开,即可入碗上桌,佐以鹹菜、油潑辣子食用;而到了稍微講究些的天水、陝西,漿水是要先嗆鍋再下面,蘭州人則是把熗炒過的酸菜當作澆頭,額外還要配上用韭菜、辣椒、菠菜、芹菜炒熟的配菜;也把酸菜剁碎後炒地皮菜、木耳菜的,加上紅豔豔的辣子,拿來搭配煮洋芋、饅頭,滋味更加酸爽,還有類似火鍋喫法的漿水暖鍋。
 電視節目《致富經》
電視節目《致富經》
漿水菜家族裏,賣相最好看的當屬漿水魚魚了。漿水酸香、酸菜脆爽,面魚在其中自在遊動,配合這一西北風味十足的名字,瞬間就能點燃西北遊子的鄉愁。不過,我家裏是從來不會做這道面食的,原因是母親不會,也不學,我也偶爾只在同學家才品嘗過。作爲粗糧細作的典範,漿水魚魚用料可謂豐儉有人——最上爲蕎麥澱粉、土豆澱粉與黃豆澱粉,其次爲玉米面,最次就是紅薯澱粉。
魚魚也叫漏魚,說的是它的制作過程,要先把熬好的澱粉糊放在漏勺上,從孔洞處擠壓到冷水裏定型,成爲蝌蚪形狀的"漏網之魚",然後再放進煮沸的漿水酸菜湯裏,調上些蒜末、油辣子、韭菜的臊子,一口酸香提神醒腦,入口Q彈,飽腹感十足還熱量不高,最後再捧着大碗把湯汁仰脖子喝光,那真的是"攢勁滴很"!
不過落在外地人的眼中,漿水還是脫離不了餿水的範疇,尤其是不嗆鍋的漿水酸菜,那股子酸爽的盡頭,不亞於米醋入腹,一股寒战直頂到天靈蓋,根本無暇分辨其前調酸香,中調甘甜,後調清香了。實際上,漿水口味的決定因素很多,最終的成品風味,更是千姿百態,過程中更是有很多講究的細節。
 圖 / 攝圖網
圖 / 攝圖網
比如容器不能沾染油污,漿水缸也不能蓋死,也不能不蓋,而且投好酸菜之後,隔天就要攪動一下;蔬菜燙過之後,可以去除葉片上的苦澀味道,但是火候要注意不能太爛也不能太生,太爛則酸菜口感不佳,難以下咽;太生則漿水不香,又苦又酸,甚至一年四季的漿水風味也不盡相同,例如夏天的漿水更甘甜,投放取食的頻率也要更快些;冬天投酸菜要多放點面粉,這樣出的漿水有些黏稠,菜多味濃,人喫上好過冬。
以上既是在家自制漿水失敗多次的心得,也是從記憶深處泛起的吉光片羽,只是那個她們心目中長大了找婆家、給丈夫和孩子臥一缸好漿水的女子,後來離那片生養她的土地越來越遠,唯有漿水酸菜獨特的酸味將她與那片貧瘠卻熾烈的土地緊緊相連。有人說,西北人走到哪裏,漿水缸就背到哪裏。
這句話也不盡然,也許是因爲孕期的特殊,讓曾經喜歡的味道,又一次佔據了味蕾的上風;又或者新生命的孕育,讓她重新找回與土地之間的聯系——某種程度上,她和世代西北人一樣要感謝那口漿水缸,感謝山裏遍布的野菜,感謝土地的出產,讓她和她的先民們"三斤辣椒十斤鹽,一缸漿水喫半年",蹣跚又頑強地繼續生活、勞作、繁衍下去。
鄭重聲明: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,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,如有侵權行為,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,多謝。
標題:漿水酸菜,一股子酸爽直頂天靈蓋
地址:https://www.100economy.com/article/83991.html